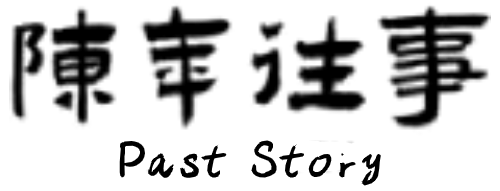一九二零年五月,毛泽东经过一番游历,终于到达上海。在上海他和另一个人碰了头,这个人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,将来他还要曲折地接手这个人的工作,再冤枉他、批判他几十年。
这个人必须专门介绍一下。
在中国历史上,有过一个书生,他剑胆琴心,刚正不阿,却遭人陷害直至开除下岗,两个儿子受尽酷刑惨死屠刀(乱刀分尸砍死,蒋介石亲自下令不许收尸),国共内战多年,他是唯一一个被捕时,国共两党都幸灾乐祸的人;最后因为抗战出狱,却既不去延安当泥菩萨供着,也不接受蒋介石的资助,贫病交加死扛到底也不改一点气节,用当年明月评价陈友谅的话来说,“端的是一条好汉!”
这个人叫陈独秀。
陈独秀,原名庆同,字仲甫,一八七九年生于安徽安庆。从小他就没有父亲,只能跟着祖父修习四书五经,邻里街坊都说那是他的“白胡子老爹”。
同毛泽东一样,陈独秀也是不招人待见的孩子,一直就很顽皮,而且无论怎样打都是一声不哭,把祖父气得发狂。老头子对他的评价十分吓人,说是“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,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,真是家门不幸!”(原话),而邻居的评价则是:“这孩子长大后,不成龙,便成蛇”。
成龙成蛇还不知道,至少陈独秀成了秀才。十七岁那年,也就是一八九六年,他考中了秀才,来年又进杭州的中西求是书院学习。
这个孩子要成为强盗的预言似乎是真的,因为他两年后被书院开除了,罪名是言论反清。
不能享受国家的公费教育,又没有言论自由,陈独秀当真开始了一系列造反生涯。
现在还不十分清楚陈独秀做了什么事情,总之陈独秀在当地混了两年,搞反清宣传可能有了点成效,因为他被官府盯上了,在安庆当地遭到通缉(肯定不是小事),只好逃到日本。那时去日本也没什么特别的手续,买张船票就能走人,要是象现在又是护照又要签证,档案里满是黑材料的陈秀才估计是没戏的。
陈秀才在东京先是找了家学校读书,两年后又溜回上海,帮章士钊主编《国民日报》,第二年看风声不紧,偷偷回到安徽芜湖,办《安徽俗话报》,次年开张了第一个反清帮会:岳王会。
陈独秀年轻的时候中国还没有政党,所有团队都要走黑社会,连孙大总统孙中山也做过致公堂(北美黑帮)的洪棍大哥,所以开帮会立香堂并不丢人,反而是光宗耀祖的好事。陈总舵主在岳王会当了一年总会长,又被官府盯上了,呆不下去,只好再奔东京逃难,先学英语、后转早稻田大学,混到三十岁、也就是一九零九年的时候,居然化身海龟成功人士,到浙江陆军学堂当了老师。
通缉犯怎么变成了军校的公务员,实在是件搞不明白的事情,很明显陈独秀虽然是秀才,脑子却一点也不生锈。别人还把留洋当成投靠洋鬼子卖国的时候,他已经发现了里面的实惠,并成功开拓出国际国内一系列人脉,可谓是造反有方。
很快到一九一一年,辛亥革命来了,清政府也狼狈下台了,陈老师凭着他的反清资历和海归名望,当了中华民国安徽省都督府首任秘书长。随着袁世凯大总统排挤国民党搞独裁,陈秘书哪里咽得下这口鸟气,当即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“二次革命”,失败后被抓起来坐牢,第二年从号子放出来,立马再度跑到日本避难,这回总舵主不读书了,改行帮章士钊办《甲寅》杂志。他写文章用“独秀”笔名,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,从此人们管他叫陈独秀,而不是陈庆同。
一九一五年九月,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《青年》杂志,一年后改名《新青年》;一九一七年初,北大校长蔡元培走后门把他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,第二年十二月,又同李大钊等创办《每周评论》。
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八年,纵观陈总舵主的经历,就是在办报-造反-逃亡-海归再办报-再造反的圈子里打转,间或夹杂着去牢房走个过场。这种日子听上去颇为浪漫,却是一点也不舒服,尤其是穷得一塌糊涂。据记载,陈独秀混到三十来岁的生活,不过是“三餐食粥,臭虫满被”,典型的酸秀才形象,比毛泽东还不如。
但陈独秀不在乎,他有一句牛气冲天的话:“我办十年杂志,全国思想都要改观!”
这句话由他说出来,就不是吹的了。陈秀才的思想超前锋锐,办杂志不是为了钱,而是推行社会不安定因素。正因为这个原因,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被通辑、被逃亡,却始终不肯放弃;而十余年努力播下的火种也没有白费,直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绽开的思想火花,陈教授并在这场运动里光芒四射,用自已的人格为中国青年写下了光彩照人的新篇章。
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号,四十一岁的北大教授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屋顶花园,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,号召造反推翻北洋军阀统治,终于被当局抓捕入狱,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。
北京大学是中国最高学府,文科学长居然凌空散传单宣扬造反,当即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。陈独秀则愤愤不平地说:学来的东西就是要用的,要是天天缩在家屋,象冷血动物一样漠视社会,就不配新青年的称号!(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,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,乃中国旧式之书生,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!)
并不年轻的陈教授一辈子都以“新青年”自居,以天下为已任冲锋在前,所以他虽然穷困,虽然没有文凭(去北大上岗的文凭是假的,蔡元培明知有问题,但人才难得,硬是留下了他),却一直斗志不衰。第二年春天陈独秀出狱,在北京已经呆不下去,他只好去上海谋出路,这时有一个人也到了上海,声称自已是李大钊介绍来的,要找他有事情。陈独秀接待了他,很快两个人就谈得非常投机。
来找陈独秀的是个老外,叫维金斯基。他的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,两个人谈的事情也很简单:南陈北李,建党救世。
陈独秀和李大钊从此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程。他们清楚地知道,将要走的那条路步步荆棘,个人会死亡,家庭会破裂,每个人都可能失掉所有。
但无论如何,国家已经如此不堪,不能再袖手旁观、无所作为。做,也许是死,但不做,大家都一定会死。
要死,让我先大众而死。
这是先驱者的真实想法。无论后来的路是否偏离,无论奋斗的结局如何,他们的勇气与付出始终是值得敬佩的。
一九二零年五月,穷游完毕的毛泽东来到上海,见到了陈独秀。
毛泽东在北京就认识这位大领导,这趟并不是专程来看陈独秀的,而是给另一批赴法国留学的同学送行。前面说过,曾经有人劝他一块留学,却被他拒绝了,因为他感觉未来的答案不在法国,但是怎么才能找到实现理想的答案呢?
他来见陈独秀就是找答案的。
陈独秀很忙。远东局的维金斯基在和他讨论如何建党,他只能抽时间见毛泽东,顺便送几本社会主义的书做启蒙,鼓励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当然,毛泽东眼前的第一步不是入党,而是考虑到哪里吃饭。
陈独秀自已都穷得要命,自然不可能给毛泽东发工资。可怜的毛老师东转西转,只找到一家洗衣店当小工,月薪十二元,扣掉坐车的费用后,只剩下区区四块钱。
毛泽东当然不是为这四块钱呆在上海的。他来上海之前已经和人联系过,打算试验一种叫改良社会主义的东西,具体做法是同几个朋友合租一处房子,在里面过所谓工读团的生活,一同上班、一同吃饭、一同看书。
无情的事实证明,生活不是生产线,大家各有各的性格,划不进统一的框框里。很快工读团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,只能散伙,毛泽东的第一次社会试验也受到严重的打击。但正所谓有失必有得,虽然毛泽东丢了工作、散了工读团,却得到一个意外的大收获,足足让他舒服了好些年。
当湖南的驱张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,有人正在信心满满地跃跃欲试,打算把张敬尧赶走,自已做湖南王。
想赶走张坏蛋的人很多,其中最得力的是前任湖南都督谭延闿,而谭都督手下最得力的师长叫赵恒惕。对谭都督来说,赶走张敬尧不仅要靠枪杆子,还要有中央政府点头才行,否则张大帅找到中央做靠山,上面派兵干涉的话,自已仍然讨不了好去。
北洋政府虽然是一帮军阀,但军阀也是讲关系义气的,要在湖南做草头王,就必须让领导同意张敬尧走人。因此除了舞刀弄枪之外,谭延闿和赵恒惕还需要在北京搞点高层公关的活动,他们选中的帮手是多年相交的老朋友、知名学者章士钊。
作为那时的著名学者、同时也是著名政治活动家,章士钊早些年里一直搞反清活动,跟孙中山、黄兴等人都是战友,还在讨伐袁世凯时当过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、军务院秘书长。章秘书长对张敬尧没有好感,却是谭延闿等人的老战友、老同事,自然很痛快就答应了下来。
跑关系是要讲人情的,谭延闿十分慷慨地给了一大笔经费,让章士钊看情况随便花,相机行事。
谭督军出手大方,章士钊也不含糊。拿到钱后,章士钊立刻四处走动,琢磨如何制造张军阀的不利舆论、协调各方面活动,这时有人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他面前:毛泽东。
说起来章士钊实在是关系广博,不光是谭延闿的朋友,也是杨昌济的好朋友,毛泽东则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兼女婿。杨教授虽然逝世了,生前却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,希望老朋友能帮忙资助留学生勤工俭学的事情,看到一脸英气的毛泽东和故友的信,章士钊顿时有了主意。
对于留学法国,章士钊并没有太多钱去资助,但毛泽东既然是驱张运动的代表,自然可以用另一个名义去帮忙,也不算辜负故友的期盼,章士钊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
钱我有,不过是办另一件事,你有兴趣吗?
毛泽东也笑了。对付张敬尧这种混蛋,他当然有兴趣。
章士钊点了点头,然后把谭延闿的钱交给他:两万大洋。
拿到钱的时候,毛泽东吓了一跳。两万块大洋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,堂堂北洋火柴厂当年筹建的时候,股本金也不过两万,月薪十二块的毛泽东突然多出这笔钱,等于一夜变成百万富翁。当然毛泽东也知道,军阀的钱不是好拿的,虽然章士钊给钱的名义是资助留学,但如果不在驱张运动里弄出点成绩,肯定有人不会放过自已,甚至可能连累章士钊,毕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,一点事不办,似乎也说不过去。
正当毛泽东手握两万大洋存折、踌躇满志的时候,突然从湖南传来好消息:张敬尧倒台了。
这一年的六月底,湖南地方系军阀谭延闿成功赶走张敬尧,成为新一任湖南王(很快又被手下的赵恒惕赶走),北京的中央政府果然心平气和,没有说一个不字。谭延闿开开心心地当上了湖南督军,在上海洗衣店混日子的毛泽东也兴高采烈地回了长沙。谭督军当然不会小气兮兮地找章士钊要回那点钱,而且对同一立场的小兄弟还十分够意思,大手一挥给了毛泽东一份校长的工作(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),不久又聘他做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班主任。
一个中专毕业生,赤手空拳地掺和到军阀混战里头,平白无故发了两万大洋横财,还捞到一个校长的职务,也就算是成功人士了。十年以前,毛泽东强行离家、跑到县城里读小学,受尽同学白眼;十年后,他凭着小小的中专学历,空手套白狼地当上小学校长、中学班主任,手握两万大洋巨款,可以说是功成名就、志得意满,毛大爹九泉有知,也该欣慰地咧开嘴笑上一场:他家石三伢子终于出息了。
从流行的成功学角度来看,毛校长的前程非常远大,他应该和军阀们搞好关系,成为一个人脉深厚的所谓专家,学术政治两不误,甚至有兴趣的话混入军政界,弄个幕僚来干干也可以。总之多求进步、努力上爬,只要马屁拍到了位,自然金钱大把、美女如云,这辈子的人生价值就算是超额实现了。
毛泽东不是不懂享受生活的人。做校长的薪水特别高,他于是找了个月租十二块钱的大房子,体体面面地接回了杨开慧,开始逍遥的二人世界:孤零零地漂了这么多年,终于能享受一把,兄弟我不容易啊!
有钱实在好办事,毛校长又是喜欢折腾的人,很快开了一家书社,大量卖有关俄国革命的书,并在陈独秀的指导下,依照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建立团组织。
有钱、有权、有书社,讲的话也有人听,毛泽东的生活从来没有这么逍遥过。
手上有书社和杂志社,身边有一群人围着讲马列主义,当校长的薪水又高;老爹逝世后,毛泽东在家里是长男,无形中他就是新的家长,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,在家里都有讲得起话的资本。毛泽东立刻安排二弟毛泽民进入第一师范、三弟泽覃去另一个中学读书,还把继妹泽建送到附近衡阳市一所师范学校,准备来个全家革命,拚出一个新中国。
很快到了六月,毛泽东在湖南的工作一步步干着,他手上已经有三十九名团员了。这个月月底,有人告诉他一件事:开会。
这个会不是一般的会,而是决定建党的会。换句话说,参加会议的人要决定建立自已的政党,从此拥有自已的组织,他们将以全新的身份活动。
对毛泽东来说,这当然是个大好消息,他马上同何叔衡去上海,在那里见到了其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。本来要让陈独秀主持大会的,但是陈教授在广州太忙,李大钊也赶不过来,只能让包惠僧代他张罗,由张国焘任主席主持。来开会的不光是中国人,还有共产国际两个代表马林、尼科尔斯基,毛泽东资历太浅,只能发挥他图书登记的特长,做一个不显眼的会议记录员。
从正史上看,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大会、是一次团结的大会,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,获得了一致的意见,进行了广泛的拥护,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,走向光辉正确的解放之路,并在后来每年举办活动,纪念这次伟大的会议。
正史永远很丰满,现实也总是很骨感。六月的上海热得要命,参加秘密会议的代表们闷在小小的房间里,一面相互认识,一面讨论中国革命到底是马上组织城市工人暴动,还是渐进式教育工人,最要命的是革命活动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注意,所以他们时不时还要小心租界的侦探。
拿一种没实践过的主义开研讨会,搞改变社会的纸上谈兵,俄国的代表也不懂马克思主义怎么在中国实施,加上天气热得吓人,实在是件为难的事情。更为难的是开会的十三个代表根本做不了什么主,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由共产国际同缺席的李大钊、陈独秀决定,甚至洋气的陈公博心思根本没花在开会上,而是同新婚的妻子四处游乐。
一群南腔北调的人,一种莫名其妙的主义,加上几个需要翻译的外国朋友、时不时出没的租界探子,这种会开得无比头痛。毛泽东六月底就到了上海,七月二十三号代表们才全部聚齐,在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开会,房间又小又热,汗臭熏天。“大”会开到三十号,终于租界警察也产生了怀疑,开始上门拜访,一群活动家只好集体出逃,坐火车去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。最惊险的是临转移的时候,开会的陈公博夫妻遭到跟踪,费了好大劲才摆脱,看到这么危险干脆不去开会了,此后也一直自由散漫,终于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。
虽然经历很曲折,但是毛泽东很高兴。冒险对他来说不是什么稀奇事,而且去嘉兴的路上还多了个伴:湖南留学的老相识萧瑜正好从法国回来,两个死党有机会坐下来一块聊天。毛泽东力劝萧瑜也参加会议,不过萧瑜显然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意义的大事,反而说自己没兴趣参加,只记得开会那天毛泽东回来得很晚,什么都没说就睡下了。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,从此两个关系很铁的湖南才子分道扬镳,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。
对毛泽东和所有人来说,在南湖开会都是件舒服的事。船上很凉快,还有各种东西吃,大家一面尝鲜鱼,一面在凉风中谈天,喝着清茶定下了几件大事:他们要建的党叫中国共产党,经过选举,陈独秀、张国焘、李达组成党的中央局,由陈独秀当书记,决定组织工会,领导工人运动。
不管开会的十三个代表将来各走怎样的路,他们都是在年轻有前途的时候,怀着社会责任和信念去冒险和奉献的,所以我认为,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来,作为当年努力和决心的尊重:
李达、李汉俊(上海)、张国焘,刘仁静(北京)、毛泽东、何叔衡(长沙)、董必武、陈潭秋(武汉)、王尽美、邓恩铭(济南)、陈公博(广州)、周佛海。
毛泽东的心情很好,不是小好,是大好。
有钱,有职位,有组织,有纪律,毛泽东作为湘区党的负责人,很是起劲地干了两年活,这两年也是事业最顺的时期。他在湖南办夜校、教工人识字和组织工会,又办湖南自修大学,秘密发展组织共产党员,还把手伸到了江西萍乡,那里的安源煤矿有一万多矿工,每天劳作十几小时,工资低廉,生活困苦,是搞工人运动的理想对象。
很快冲劲十足的共产党员李立三就到了安源,后来又陆续赶到刘少奇、蒋先云、黄静源、毛泽民等人,毛泽东也几次前往安源办工人学校,组织工会、工人俱乐部。不到半年时分,安源的工人成立了工人俱乐部,湖南则成立了团结工会,在赵恒惕两万大洋的帮助下,从安源到长沙,各行业的工人都学会罢工了。
连年军阀混战,湖南督军赵恒惕一直很忙,毛泽东也就顺利潜伏下来。一九二二年,中共第二次大会召开的时候,毛泽东没能参加,据说是因为活动太过保密,毛校长来了上海却找不到组织,只好买车票回家。二二年的十一月,毛泽东已经成立了湖南省工团联合会,自已担任主席,还能发布宣言通 告全国,这时中国共产党手上象样点的组织只有两个,另一个是 湖北省工人团结联合会,负责人的名字叫向忠发。
毛泽东的成功没有持续多久。张扬到一九二三年,赵恒惕终于感到不妙,四处发起的工会严重制约了老板们盘剥的自由,更可怕的是自已的权威受了影响,对于军阀来说,这类事情是没有商量的。
虽然是驱张运动的同道,但毛泽东显然不再有任何价值,而赵恒惕的忍耐也到了极限。这一年四月,毛泽东悄悄离开长沙去了上海,街头上已经有了通缉他的告示。
逃到上海的毛泽东并不孤单,他见了一位老朋友:一块开建党大会的马林。两个人相约去了广州,在那里陆续又见到了几个老朋友: 陈独秀、李大钊、张国焘、谭平山、蔡和森、陈潭秋、罗章龙…
这么多造反专家聚在一起,很明显不会做什么安分的事情,原来是中共要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了。很快在一九二三年的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,在广州东山恤孤 院后街三十一号召开了三大,毛泽东以湘区党代表身分出席,大家从容地选出陈独 秀、毛泽东、罗章龙、蔡和森、谭平山当中央局(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)成员,陈独秀是中央局委员长,毛泽 东则代理中央局秘书,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规定,“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,并管理本党文件。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”。
这句话的意思是说,这个时候的共产党,所有文件没有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字就不算数。
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。这一年他三十岁,刚好是而 立之年。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,这些年的辛苦终于有了点盼头。
但是三大的意义绝不在于选了毛泽东当秘书,而是一个重要的决定:共产党无限责任公司要集体加盟到另一家叫国民党的大型集团里面,服从总裁孙中山的领导。
几十年风云际幻,上百万人兵戎相见,无数家园沦为荒丘,整个中国至今一分为二,全都从这个决定开始,而要说这次合作是怎么回事,就得从那个叫孙中山的总裁说起。
让我们先看一看孙中山的简历。
孙中山,一八六六年生,广东香山县人。小时候叫帝象(不安分的名字),学名“文”,字德明,号日新,后改号逸仙,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,因此也叫“孙中山”。
孙中山十三岁时,跟老妈去了夏威夷的大哥那里,在当地教会小学读书(免费的),十五岁想信基督教,把大哥吓得够呛(那时信洋教是离经叛道的事情),赶紧把小弟送回国,此后到香港找了家克莱登式的学校念书,叫香港西医书院。
从历史上看,西医书院应该是很差劲的,因为孙中山二十六岁毕业的时候,那一年毕业生只有两个。更要命的是西医书院没有立案,得不到香港当局的承认,当然也拿不到官方的行医执照,只能给人打下手。
本来想好好混生活,结果前途被劣质民办教育毁了,无牌医生孙中山过不上安分日子,只好另谋职业,做点不安分的事。
小孙大夫二十八岁的时候正是一八九四年,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的年代。他先是给李鸿章上书要求改革,被拒后跑去檀香山组织兴中会,提出“驱逐鞑虏,恢复中国,创立合众政府”的口号,开始了一系列造反历程。
一八九五年三月,孙中山在广州策划第一次起义未果,被清廷通缉,香港也呆不住了,只好去日本。一八九六年去美国,同年秋天去英国,被清廷扣在使馆里,后在外交压力下交出人来,反而因此声名大涨,筹集经费十分方便。一八九七年他经加拿大前往日本,又结识了一帮日本军政要人和梁启超等保皇派,一九零零年想和李鸿章一同搞独立的南方政府未果,同年九月准备在日本支持下从广东造反,结果日本态度变化,失败。一九零三年在日本青山开军校,立誓反清,零四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,当了黑帮致公堂的高级长老“洪棍”,目的仍是反清(后来成立中华同盟会,北美移民法律限制移民的流动,同盟会有活动就是通过致公堂进行的),到美国宣传反清无果,于是接受资助去欧洲筹款,零五年再去日本同黄兴一齐反清,八月,孙中山与黄兴,宋教仁等联合各组织成立同盟会,提出“三民主义”学说,劝人革命,推翻大清国。
简而言之,孙中山这些年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:造反。
清朝政府当然不傻。慈禧老大妈打仗虽然不行,维稳还是有点本事的。在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,有关部门很快就盯上了孙中山,并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,要求日本政府以清日关系大局为重,采取措施阻止一小撮反清势力的干涉与颠覆,切实尊重大清主权和权益不受影响。日本不愿意为一个人得罪一个政府,只好找孙中山商量,说你在我这里很有麻烦,直接赶你走又不大好意思,送一笔钱给你到别的地方“读书”吧。
孙中山具体拿了多少钱不大清楚,有的说法是一万多块,总之数目不会少。不管怎样,反正他拿钱后去了美国,继续当他的黑帮洪棍,四处拉人造反。因为拿钱的事没跟同盟会商量,会里吵得热火朝天,纷纷说他贪财,孙中山一气之下还跑到南洋,同胡汉民、汪精卫两位小弟另外成立了同盟会总部。
马克思曾经曰过,经济是政治的基础,这句话实在一点也不错。历史记载着孙中山解决经济问题后的一系列“职业”生涯:
一九零七年五月,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,历六日而败,这是第三次起义;随即六月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(今天的惠州市汝湖镇),历十余日而败,第四次;七月六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,失败殉难;同月,孙中山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,再告失败,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,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踏足中国国土;一九零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,第七次起义;四月,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,第八次;一九一零年二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,第九次。
这是一份屡败屡战的简历,也是一份剽悍人品的证明。孙中山和陈独秀从本质上讲是一类人,但他们的方法却是完全两样,陈独秀想先唤醒民众再选造反,孙中山则要生猛得多,打算直接造反后再唤醒民众。不管谁对谁错,结果都是一样的,就是失败,孙中山大半辈子的生活,大致说来就是造反-逃亡-再造反-再逃亡。
屡败屡战不是没有代价的。从海外找人捐款的时候,孙大洪棍没有资本,唯一的许诺是将来成功后一定给回报,反复失败后大家渐渐明白了,造反这种事实在不靠谱,国家领导也不是说当就能当的,眼看投资都打了大水漂,广大人民群众干脆给他取了个外号叫“孙大炮”,笑他成天忽悠人。
一九一一年,孙中山终于走到了人生的低谷。四十五岁的致公堂老大混得穷困潦倒,身上找不出几文钱来,只能跑到餐厅里洗盘子打工混饭吃。没想到正在这一年的十月,湖北武昌爆发起义,同盟会势力迅速在南方建立政权,山西的阎锡山趁机倒戈反清,顿时南北交通断隔,半壁江山突然宣布独立,朝廷一下子慌了手脚。
看到形势一片大好,孙中山大喜过望,赶紧坐轮船回国参加革命。他一到国内,同盟会立刻推选他当了临时大总统,定下新国号“中华民国”,并制定了民国约法,准备再接再励、革命全国。
昨天还在洗油腻腻的脏盘子,今天就黄袍加身当了大总统,孙中山实在是喜出望外。然而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,他很快回过神来,俗话说天下没有白掉的馅饼,总统绝对不是白当的。武昌起义不是他指挥的杰作,大家之所以肯把宝座让给他,不是请他享受权利,而是要他承担义务,具体来讲是希望他能帮忙背黑锅。
当孙大总统喜气洋洋地上任时,清朝政府并没闲着。毕竟大清国帐面上有一百多万大兵,尤其是精锐的北洋军丝毫未损,此时正气势汹汹地逼进武昌,准备把“叛军”一网打尽。面对大军压境,一盘散沙的起义军根本招架不住,临时抬出一个孙中山,是希望他有妙方能解决问题。
作为满清政府真金白银砸出来的精锐部队,北洋军是孙中山无论如何扛不住的。
所谓北洋军,是李鸿章在淮军底子上建起来的新式军队。按清朝当时的地理划分,从吴淞口往南的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算南洋,而往北的山东、平津及东北都叫北洋,李鸿章在北洋几个省建的部队,而部队司令又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,这支军队就叫北洋常备军,简称北洋军。
北洋军的实力有多强,可以从数字上看出来。当年的北洋军每个师(当时叫镇)有一个炮兵团,每团三个营,共计七五口径野战炮十八门、山炮三十六门,还大量装备当时的先进武器–水冷重机枪,而且不象后来的军队经常吃空额,这些师的炮和士兵都是齐装满员的。
一直到几十年后,蒋介石手上装备最精良的所谓中央军,一个军也不过十二门七五山炮,已经算是火力强大;抗战胜利后靠美国援助的所谓国军五大主力,一个师的七五炮仍然不超过十二门,只有最精锐的军级部队才有八到十二门一零五炮,对比北洋军一个师五十多门七五口径大炮,简直就不好意思打招呼。而且北洋军时代是旧中国军工的黄金年代,大炮不是进口就是用进口设备按国际标准严格生产,性能绝不落后,随着北洋军阀的倒台,中国进入几十年战乱年代,炼钢厂也纷纷关门,留下来的底子一点点耗尽,中国军队装备不上国产大炮,更赶不上北洋军的标准,重火力一落千丈,一直到一九五零年后新中国全面引进苏式装备,这才算改善过来。
在清廷眼里,北洋军就是他们的王牌军,来而能打、打而能战、战而能胜,是朝廷的威武之师、雄壮之师、胜利之师、维稳之师。面对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北洋军,就是国际列强也要给几分面子,临时凑起来的南方起义军自然更加不用提了,更为严重的是起义军不光装备差,连军饷都发不出来。
几个独立出去的省并没有多少积蓄,清廷当然也不可能给他们发钱,临时政府发不出军饷工资,急得四处找日本和列强借钱,无奈好话说尽,对方就是摇头不答应。南方革命党急着让孙中山当总统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为他有大笔海外捐款救急,谁也没想到孙大炮是从厨房放下盘子赶来的,啥也没带来,还要拿总统的薪水吃白饭。
出来混,没钱是不行的,南方起义军接连战败,汉阳也告失守,北洋军很快直逼武昌。孙大总统上岗的时候,南北两军已经开始谈判,南方政府被逼表态,只要袁世凯反清,可以选他当大总统;等到孙中山赶来当临时总统的时候,面对清朝政府军司令、北洋大臣袁世凯咄咄逼人的进攻,他只能继续谈判。
孙中山Vs袁世凯,两个世纪强人开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:你行,还是我行?
对这个问题,基本上是不用多猜测的。
如果硬打,最多北洋军和革命军两败俱伤,满清朝廷可以坐在一旁喝茶,毫无违和之感;如果不打,军机大臣袁世凯倒也愿意参加造反,但是袁司令的要价极高,他要求当未来的民国大总统。为了解决前线的经费,孙中山被逼得没办法,甚至急得答应把中国东北押给日本,用来换应急的军费,可日本考虑到南方政府的兑现能力,始终是钱袋紧捂,一分钱赞助费都不掏。
实力决定一切。孙中山没有实力,所以他只能答应袁世凯的条件,只要袁司令能让清朝滚蛋,大家可以在民国约法的基础上拥护他当大总统。他的想法很简单:不灭了清朝,中国肯定没有崛起的希望,那就先达到这一步,然后慢慢来。
从官方的历史书上看,孙中山显然是不对的,众多历史叫兽纷纷摇头晃脑,品头论足地说孙中山是搞右倾主义,对袁世凯让步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云云。
街头卖菜的老大妈这样胡诌几句可以理解,堂堂叫兽也这样认为,实在应该拖出去,好好打一顿屁股。
这帮叫兽该打,是因为他们总给些非常呕吐的评论,如此信口开河,等于存心抹黑革命先驱。孙中山虽然姓孙,却不是孙悟空的亲戚,不能拨根毫毛变出粮弹兵丁闹革命,不妥协难道要他上吊么?
很明显,袁世凯是不管右倾不右倾的。有了孙中山的承诺,他马上回宫去找老寡妇(皇帝溥仪太小,一切还是太后做主),施展他的忽悠才能。经过一番细致又周到、暴风加细雨的思想工作,袁司令连吓带唬地哄太后发了一个逊位诏书,宣布朝廷现在不想理政,所以暂时关门盘点,国家大事交给大家去操心。
虽然只是“暂时”关门,没有明说下台,可所有人都知道,大清朝这一跤是栽到了坑里,再也别想翻回去。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号,也就是发布逊位诏书的第二天,圣寡妇皇太后还习惯性地上班,傻傻地等军机大臣袁世凯早朝汇报工作,等到中午也不见人影,就派太监去催。
太监当然不敢怠慢,气喘吁吁地跑了一趟,然后回来禀报说:袁世凯回话,从今天起,不用来早朝了!
太后毕竟是太后,过了半天终于反应过来,顿时坐在椅子上又气又急,最后失魂落魄地丢下一句话:“大清的天下,难道就亡在我手里了么?”
老寡妇越想越害怕,越怕越难过,坐在椅子上哭了一场,又稀里糊涂地让太监掺回去睡觉。她这才明白,从昨天发出那道要命的诏书时起,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、残害禁锢整个中国的封建清朝,已经半忽悠半认真地宣告完结了,而她则是列祖列宗最后的那个送终人。
老太后哭哭啼啼地回宫里拜祖宗,袁世凯高高兴兴地当总统,孙中山则恨恨地咽下了一口气。袁世凯有钱有枪,他却什么也没有,只有一本刚刚印出来的民国约法。
转自天涯:红潮笑笑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