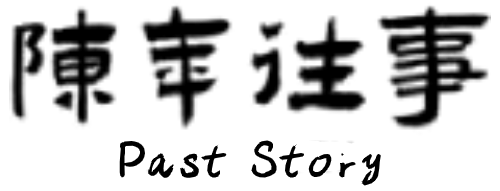在北平的张作霖很头痛。
他在东北自立为王已经很多年,一方面是自已有手段、有野心,另一方面也是日本人的援助。为了吞并东北,日本人已经下了很多本钱,给了很多军火,当然,也要了很多特权。
虽然花钱有收获,但总地来讲,张作霖在信用方面,名声是不大好的。每次找日本人要东西的时候,都会连连点头,把日本人当大爷敬;等拿到钱和军火之后,立刻开始耍无赖,不是当面抵赖,就是让属下使绊子、设障碍,总之地盘是我的,东西也是我的,你不能拿走。
起初的一次两次,日本人觉得张作霖做人有点贪;年复一年地耍赖,日本人也回味过来,张作霖不是犯傻,这个叫信用问题。
发现自已被骗了,日本人很生气,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,后果都还不算严重。因为东北已经成为张作霖的私人地盘,扶持他又花了那么多血本,没有张大帅,就要重新喂饱另一头饿狼,从成本核算的角度上看,这个开销不太值。
所以张作霖耍奸使诈、说话不算数,日本人都只是笑笑装傻,什么也不说。而这一切也给了张作霖危险的错觉:日本人是需要我的,东北也是需要我的,我做什么都是没关系的。
事实上张作霖确实没法听日本人的,因为对方要他做的事十分要人命:在东北搞独立,做日本的儿皇帝。
在东北搞独立,涉及到另一个严肃的问题,就是国家和主权归属。
虽然各路军阀都喜欢占山为王,也都把地盘当成自已的私产,但毕竟大家还都承认自已是中国人,不管听不听中央政府的号令,祖宗是不能不认的。不管谁当家、谁上台,都宣布自已是中国的合法政府,或者中国某地的合法政权,但很少干一件事,就是另立国家、不承认自已是中国人。
当然,某些外国(例如日本)会认为,这是一种落后的封建思想。但不管哪个军阀在台上,都摆脱不了这种落后思想的束缚,也不敢按外国人的指令分一块地盘出去搞单干,所以中国才能以大一统的姿态飘摇下来。说白了,当个草头王是可以的,不认祖宗不当中国人是没门的。
虽然张作霖是个唯利是图的土匪军阀,但他绝不肯走出那一步,而在重重的幕后,日本人的耐性也到了极限。
鬼子根本不是想在东北要什么特权,他们是想把东北变成他们的一部分,张作霖已经由棋子变成了不听话的棋子,应该从棋盘上撤下去了。关东军相信,张作霖一死,手下肯定分崩离析,很快他们就可以进军全东北,在城头插满太阳旗,而那个时候,蒋介石将无能为力。
害死李大钊和邵飘萍等人的奉系土匪军阀张作霖。他死后不久,不争气的儿子就败掉了东北的家当,把中国拖进深渊。
一九二八年六月三号,张大帅坐着专列,从北平撤回关内。
张作霖很清楚,他的首席赞助商–日本并不赞成他回东北,因为奉系如果放弃华北,中国将有被国民党统一的危险,也会大大增加吞并中国的难度。但他更清楚,呆在华北同蒋介石死磕,很可能被国民革命军活活磕死,而以他那个绣花枕头般的少帅儿子,是绝对镇不住局面的。
在此以前,日本人已经容让了他无数次。所以张作霖相信,这一次也不例外,日本人仍然会皱皱眉头,然后任他行事,无可奈何。
作为草头王,张大帅对自已的安全进行了严密的保护,不仅出发时间保密,而且行程一日三变,沿途更是精心护卫,生怕有人劫车。
当然,所谓严密,不过是张作霖自己的感觉而已。事实上他的专车什么时候准备、什么时候出发,站台作业都是明明白白,只要有人去看一眼,就能猜得出来。而张大帅严密安排了半天,却仍有一段地方没办法保护到位,因为那一小段铁路是日本人的地盘,中国兵不能进去执勤。
中国人不能进入的中国地方,叫皇姑屯。
虽然没有保护,大帅还是很心安,日本人是他的老朋友,虽然有不少冲突,可交情毕竟还在,而且东北除了自已谁也玩不转。
带着十足的自信,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出发,开向皇姑屯,然后在那里收到了日本人迎接的礼品:大批埋好的炸药。
所谓大批,是指一大堆,确切地说,一百二十公斤,装了几大麻袋。
张作霖的专列有整整二十节,保不齐爆炸的时候大帅在车头或车尾,所以要炸就必须把整列车厢全部送上天。关东军为了干得专业点,专门从朝鲜调来了工兵,好不容易才装齐这一大堆累赘,张大帅以为自已隐密回家的时候,日本人正沿路监视,等着他的到来。
一声炸响,横行东北的张作霖飞上了天空。
对张作霖的死,日本人早有准备。他们在附近准备好了尸体,上面写着孙中山的两句遗言,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犹需努力”,然后宣布,这两个便衣是蒋介石的特务,要对张大帅的死负责;至于日本,因为他们的铁路被炸毁了,所以同样是受害者。
蒋介石派两个特务溜进日本人的防区,扔了一枚均匀分布二十节车厢、重达一百二十公斤(注意数量)的炸弹,把张大帅的专列炸死,这就是关东军对整件事情的官方解释。
收到父亲的死讯,张作霖的儿子、还在北平的张学良第一反应不是居丧,也不是报仇,而是立刻把头发剃光,背着大锅化装成士兵,连夜潜回沈阳。
这回再不敢张扬了。
沈阳的东北军阀们正在开会。同日本人想的一样,他们并不想让张学良当新一任东北王。
虽然子承父业,但时代在发展,社会在进步,早就不是封建时代了,大家的意识也在进步。更重要的是,张作霖做事有手段有魄力,张学良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子哥,虽然他也很努力,但是,他真的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。
身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学良,又英俊、又新潮,不仅长得一表人才,而且多才多艺,举个例子说,他不仅会开摩托车,还会开飞机。
开飞机在那时可是高科技,不仅在中国稀奇,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技术,尤其是故障奇高,经常上了天下不来。张少帅敢开飞机,除了他老爹手上有钱有飞机外,主要还是性格问题,这个公子哥什么都喜欢尝新。
飞机喜欢尝新,女人喜欢尝新,毒品也喜欢尝新。
当然,身为军阀,张学良的爱好,或者说生活作风问题,并不是很严重。但一个人如果在很多方面都突出,必然在另外一些方面上比较短板,张学良却偏偏全身都是短板,找不到多少突出的地方。
很多人知道张学良的外号张少帅,但不少人都误会了这个称呼的意思。所谓少帅绝非夸奖的意思,也不因为他是大帅的儿子,倒有一大半是说他只长得帅,放到今天,和“小白脸”的意思差不多。
因为这个词的含义并不好,所以在当时,通常是不能当面称呼他少帅的,否则一定是大为光火。当然某些(或者说大部分)国产影视剧就不要去信了,东北的元老们心里有数,当面敢叫张学良少帅,那就是找死没商量。
出席外交场合需要长得帅,军国大事一类的还得看能谋擅断折真功夫,小张同学既不会谋,也不懂得断,长期在威风八面的张大帅手下工作,为人还有一个极大的缺陷,叫做懦弱。
所谓懦弱,是指在关键时刻、需要做决定的时候,没有担当,没有牺牲,只想逃避,混过一时是一时。
几乎所有人都有类似的缺点,但在关键的位置、关键的时刻,身为统帅的人必须克服它的不良影响,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来。然而张学良做不到。
所以东北元老并不打算让张学良做新一任领导,他们的团结目标,叫张作相。
虽然同张作霖只差一个字,张作相和大帅并没有亲戚关系。面对大家的拥戴推举,张作相只做了一件事:当着所有人的面,他把属下做好的统帅服恭恭敬敬地递给张学良,并严肃地发誓,大帅生前他忠于大帅,大帅不在了,他就只忠于张学良!
既然张元老如此表态,那就啥也不用说了,大家乖乖地让开路,请张学良坐上中间的宝座。
总地来讲,新官上任的张学良,表现还算是中规中矩。他想办法除掉了不听话的元老,努力巩固自已的权威,然后下令,东北归顺南京政府。
所谓归顺,并不是带着人马去投奔,而是宣布东北承认南京为合法中央政府,同时全东北降下旧国旗(五色旗),换升青天白日旗,史称东北易帜。
虽然只是换面旗,这个举动却有着极不寻常的含义,首先是宣告北洋军阀时代已经正式结束,其次则是用具体行动告诉日本人:你们炸死了我老爹,可我不会独立,也不会听你们的!
在张少帅乏善可陈的历史生涯中,这是他难得的一次亮点。
对张学良的做法,日本人恨到极点,但至少在目前,他们还没有办法。因为东北军有二十多万,而驻扎东北的所谓关东军,只有一万。
一九二八年十一月,在东北宣布归顺后,全中国终于又在名义上重归一统,连新疆和西藏都承认这个中央政府,包括后来一直闹独立的达赖喇嘛。
蒋介石非常高兴。在一系列明争暗斗下,他终于算是“北伐”成功,虽然没有伐掉太多军阀,但至少把大家都加到圈子里了,而在这个圈子里,他是最大的那匹领头狼。放眼天下,除了极小几处没杀尽的共产党人,全国都飘扬着他的旗帜。
短短三年工夫,从一个军校校长到全国总司令,功业杀伐,名垂青史,还有什么不满足的?!
来人哪,拿酒,拿酒来!
一九二八年底,志得意满的北伐军总司令、中华民国领袖蒋中正回到南京,出任国民政府 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。前一个头衔没什么,随手可以给别人,后一个却一直坚持了下来,因为蒋介石深刻理解到,军权实在是太重要、太重要了。
从此他也叫蒋委员长。
也正是在这一年,南京修的孙中山陵墓快要峻工了,突然市里传出谣言,说建墓的石匠要收小孩的魂魄去“合龙口”,市民于是往孩子左肩挂一块红布,写下辟邪的歌诀。
小道消息满天飞,喜欢新闻的报纸当然不会放过,还收录了三首辟邪的打油诗:
人来叫我魂,自叫自当承,叫人叫不着,自已顶石坟。
石叫石和尚,自叫自承当。急早回家转,免去顶坟坛。
你造中山墓,与我何相干?一叫魂不去,再叫自承当。
这种事当然是封建迷信,不少人都把它当成笑话看,却有一个人仔细品味报纸的歌谣,然后为小市民的机灵麻木发出剑一般犀利的叹息:
“这样的歌诀,把普通市民对革命政府的关系,对于革命者的感情,都已经写得淋漓尽致,‘叫人叫不着,自己顶石坟’,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。
“这样的民族性如果不改变,这样地牵缠下去。五十一百年后能否就有出路,是毫无把握的。”
这个人叫鲁迅。
民国是一个异彩纷旦的年代,出过无数国学家、大师、史学家,以及这种那种家,粉丝遍天下、弟子满世界,但最有思想、也最值得景仰的,是鲁迅。
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段话的时候,第一反应是去找砖头想拍人。不过不要紧,因为我相信当年的鲁迅也挨过黑砖,他能全身而退,我也能。
当年明月曾经说过,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,因为历史的内涵没有变化,几千年来该犯的错误都要犯,该死的还是要死,岳飞会死,袁崇焕会死,再过一千年,还是会死。
我于是想到,不久前曾经有一条新闻,一个大学生村官因为发些批评时政的消息,被当地警察抓了,关在狱里劳教,罪证是从箱底搜出一件衬衫,上面写着“不自由,毋宁死”六个字。据警察说,劳教的理由是这六个字反动。
这六个字,当年共产党烈士牺牲时也说过,如果要推敲的话,那帮警察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分子,然而他们横行无忌。
我们都痛恨满清的文字狱,但民国一样有文字狱;我们都声讨民国的残暴,但共和国的功臣们下场却更加凄惨;我们痛悔文革时的迫害,但时至今日,还要因为衬衫上的六个字搞政治迫害。所以我不得不相信,当年明月的话,也许是对的。
德国闹过纳粹,但德国反省自已的错误,绝不允许再犯;
苏联出现过大清洗,此后俄罗斯大批公布历史档案,向受害者承认错误;
即使是曾经施行过野蛮军人统治、且一直不肯反省历史的日本,在对待国民的态度上也比我们要强得多。而且让中国人汗颜的是,日本人其实比我们要团结,日本人靠内斗、诬陷,贬低别人抬高自已的手段并不多见,即使是所谓右翼团体,相互之间也少有拆台、造谣;而中国人最喜欢干的事却是划派系、分敌我,然后相互内斗。
中国人最精彩最热衷的节目,莫过于沾沾自喜地在圈子里相互争斗,就象郭老大的相声所言,凡事最可怕的就是同行。
翻开世界历史,能象我们这样,一遍又一遍重复错误、暴行还沾沾自喜的民族,当然不好意思说是绝无仅有,但要找出类似的例子确实很难,或者说不大可能。爱国愤青们会扔砖头,会念国骂三字经,但往往也只会这两样本事而已!
只要不从根源上反省自已,认识自已存在的缺点,就不可能消除问题,我们也要仍然会一代代重复自身的悲剧,继续在内斗、内耗以及愚昧吹捧中前行,就象背着壳的蜗牛跟别人赛跑。无论属于什么党派,无论秉承什么主义,始终摆脱不了惰性的怪圈。
从这一点上讲,当年明月说的话,一点也没错。
我总会想起那些凭一件衬衫把人送进监狱里的警察。他们何尝没有遭过生活的压迫,何尝不知道自已做的事荒谬绝伦,但只要一有机会,就会不计底线地讨好上司,象疯狗一样欺压别人,一如满清时对上司满脸谄笑、拖着辫子在衙门里作威作福的奴才。
国学大师辜鸿铭在辛亥革命之后,一直拖着脑后的小辫子不肯剪。面对北大学生的讪笑,他平静地说: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,而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。
大师奥义深妙,令人顿起高山仰止之感,学生们顿时不笑了,端端正正地听课。而我知道的是,很多人都应该惭愧、应该反省,但有一个人是不用惭愧的,他曾经用笔剪下过我们心中的辫子,而且还割开辫根下的肌体,向我们剖析毒瘤的根源,展示一个血淋淋的真实世界,那个人就是鲁迅。
鲁迅,一八八一年生,原名周樟寿,后来改名周树人。鲁迅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的笔名,但因为用得多了,大家也就忘了他的本名。
小时候鲁迅的家境还算好,可当官的祖父犯事进了监狱,父亲也卧床不起,家道于是败落下来。
从富到穷,最容易体验人情冷暖。看过父亲在中医(庸医)手上痛苦辗转,看过幸福的小家因病而贫,鲁迅立志要医治象父亲那样的病人,解除他们的痛苦,强健同胞的体魄;所以他十八岁去了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,接着到日本学医,希望能做一个医生。
在那个年代,他的选择就是把灵魂卖给洋鬼子,是不折不扣的出卖祖宗、出卖国家,爱国愤青们全都拖着辫子、抱着经籍口诛笔伐,一如现今砸车打人的所谓爱国者。但还是有很多人走上了出国的路,有的人碌碌无为,有的人功成名就,更多的人努力一生,师出未捷。
东京的留学生很多,也都拖着辫子施施然,有的学跳舞,有的学喝酒,同现在情况差不多,鲁迅却去了仙台,孤独地在医学院里读书。虽然是弱国国民,还是有不少朴素的日本人关心他,平等地对待他,给他温暖与帮助,不让他感到孤单与歧视。
鲁迅于是努力地学习医学,直到有一天,他看到日俄战争的时事电影。日本兵在中国东北当众砍杀中国奸细,周围都是些看热闹的中国人,满脸麻木地看杀。
年轻的鲁迅被震憾了。被杀的是中国人,看杀的也是中国人,而且他们都很健康,不需要医生。
鲁迅终于想到一个深层次问题。
即使中国人全都健康强壮、从不生病,也不过是杀和看的材料而已,对国家民族的进步并不会有多大改变,医生能改变贫弱的身体,却不能改变愚昧的思想。在痛苦的思索之后,鲁迅明白过来:一群健康的奴隶和一群生病的奴隶,并没有本质的分别。
这时还是清朝,同众多革命者一样,鲁迅也有维新的愿望,也有破除陈旧牢宠、迎来全新中国的渴求,而这些靠当医生是改变不了的,因为国民生病的不是贫弱的身体,而是麻木的灵魂。
他本来可以有不错的生活。家境贫寒的他已经很久没有挣到钱了,学完医回中国就是抢手的专业海归,能在大城市开自已的诊所,再娶一个日本女孩,备几个漂亮的小秘兼护士。以他的能力水平,当个名医不成问题,好车好房也不成问题,而且医生不比军阀,虽然一样是拿人命换钱,医生的风险却非常小,绝少有人真刀真枪地跟自已玩命。
在那个年代,留洋西医是金字招牌,不懂变通的他却放弃了学业,非要跑回国内教书,搞文学教育,说要唤醒麻木的灵魂。
这是一个绝对冷门的行业,至少比医学要冷出一百倍以上。
虽然有名望的教授们收入很不错,但鲁迅不是什么名人,在家乡当老师的工资也很低,加上要养家,生活一直拮据不堪。坚决不肯留辫子的鲁迅在小小的绍兴处境艰难,一直困顿到一九一二年,才靠着蔡元培的赏识,在北京教育部当了一个相当于处级干部的佥事,一个月有二百二十块大洋的薪水(注:经常拖欠),好不容易宽松了起来。
在常人眼里,鲁迅实在是一事无成。他没能当成医生,却在拮据中耗去了青春的黄金十年,然后又在北京当了十四年公务员。这十四年里袁总统称过皇帝,北洋军阀混过战,清朝皇帝复过辟,陈独秀领导过五四激情和共产建党,孙中山还当了一回又一回大总统,可鲁处长什么也没干,只管上班点到,下班吃饭。十四年时间里他的唯一成就,是薪水已经涨到三百六十大洋一个月,只要政府不拖欠工资,就算是教育部的高薪人士了。
按照流行的成功学,他应该和领导处好关系,一级级升官,同时关心一下家庭和子女教育,偶尔不妨去红灯区风流一下,最终成为某名校的校长(这个词现在已经比较危险,当年却还是有威望的)。
然而他哪样都沾不上。
他的婚姻是包办的,一点也不幸福;他和妻子朱安一点话也说不上,索性把她送回家乡,一直到四十六岁那年,才和小自已十八岁的许广平同居。
他也不想升官。十四年里教育部换过三十八个教育总长、二十四任教育次长,除了学问道德都算好的蔡元培和交情不错的董恂士,鲁迅一个也看不上眼,更谈不上巴结了。
但是不懂升官的鲁迅并没有光混薪水。除掉按点上班,他在这些年里只做了两件事:读书,写文章。
压抑,冷淡,加上童年经历过太多人情冷暖,鲁迅的笔触异常沉重而犀利。他毫不留情地描绘出五千年文明的神话下,国民心态的另一面:麻木,帮凶,窝里斗,自欺欺人,媚上欺下,自大骄狂,幸灾乐祸,得过且过…让人在文字中猛然醒悟,许多大国的虚荣传统下面,不过是教人如何做奴才而已。
鲁迅不仅刻划出奴才的形象,而且还揭露出奴才一面做帮闲、一面当帮凶的形态。在他笔下无论是维新还是守旧,骨子里都浸满封建统治的沉渣,而不能摆脱这样的束缚、用新的理念贯彻改造国民大众,便永远只能重复与麻木,扼杀奋进的精神。他毫不留情地剖析包括自已在内的中国人,揭露出中国的麻木与腐朽,用他的文章当镜子照别人,会充满优越感;但如果拿它照自已,则会一身冷汗。
奔波的鲁迅最后住到了上海,同瞿秋白、柔石等人很熟,与共产党人也多有来往。他没有去过苏联,对共产主义抱过幻想,但至始至终,他不愿加入共产党。
鲁迅不是神,他也有七情六欲,也会和人谈稿费分成,也会算计自已的进帐开销;甚至在周边朋友的眼里,他绝不是满脸凶恶的斗士,而是一个幽默近人的教授或书生。但他始终保存着一份中国文人的风骨,用自已的文采映照出超然籍口下的丑陋,留给后人一个孤独的身影,让人明白虚伪、奸诈、构陷、迷信、盲从下,国人一盘散沙的本质,真正体会到几千年封建沉淀对文化与人性的扭曲。
经历过革命与被革命的事例后,鲁迅看透了国人对权术的追求盲从,深夜间总会有一盘散沙之恐惧孤独,因为他深切体会到大黑暗之恐怖,虽与麻木的同类同持一种语言,彼此却恍如路人,不知所云。在那个存亡不定的年代里,无数青年因鲁迅的文字而惊悸,也因鲁迅的胸怀而折服。他们从鲁迅的文章里明白,倘使中国不能从民族性和国民性中省悟,则现实依然将化为权术工具与交易,只要这种本性不加改变,鲁迅的遗憾就只能依然,并注定要成为一份百年孤独。
在尘世间呐喊的鲁迅,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。
这是一份高尚的孤独。这份孤独随着文化而传承,不在身边友人多寡,而是西狩获麟、微言遽绝时的无奈,是一代热血奉献后陆沉鱼烂的结局悲哀,是看到黑暗而依然勉力牺牲、呐喊于生人间却毫无反应、便有回声也是不知所云之苍凉。拥有这份伟大孤独的人富贵亦清贫,在世如出家,注定要流浪奔波,于一切光明堂皇中看透背后的黑暗、掩饰,而在漠然与微笑间前行,面对一切诽谤与箭矢,不以伤痕为意,必持操守节,于光明浮形间消逝于大黑暗中,那是亡命徒早已选择的人生,是士人所不能违背的操节,是为家国沧桑百般煎熬于心中的火焰。
伟大而孤独的鲁迅先生永垂不朽!
在旅日学生竞相组团,相约刺杀、起义的时候,医学专业的鲁迅却认为,如果不唤醒国民麻木的灵魂,推翻一个王朝的结果无非只是塑造另一个王朝,而奴隶们的命运是不会变的。
无数社会精英慷慨激昂、前仆后继地投身革命,有的失败了,成为纪念碑上的名字;有的成功了,成为新一任军阀或政客,台下则是无数伸着脖子任人宰割的看客。领袖们轰轰烈烈的同时,鲁迅却选了另一条路:从文,用文字唤醒国民。
这是一条漫长而绝顶艰难的路,它的难度,丝毫不亚于发起一场革命。因为战争的对手就在面前,而精神革命的对手却是无处不在、无影无形,强大到令人窒息的地步,并使人无从反抗。
而家境困顿的鲁迅义无反顾地接下了这个挑战。在付出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辛与精神折磨之后,他最终获得了成功。
夸了鲁迅大半天,下面要谈一个实际的问题,就是鲁迅这么伟大,为什么中国人的心里还拖着辫子呢?
有个作家曾经说过一句话,中国之所以文化不发达,是因为文化部的领导都没有文化(大意)。这句话用在鲁迅的遭遇上,非常合适。
从新中国建立的时候起,管文化教育的领导们就把鲁迅打扮成了神,不光说得他上天入地毫无缺点,而且还做了一件极其不要脸(如果有的话)的事:曲解鲁迅的文章。
鲁迅的文章极富思想性,但再有思想,也敌不过领导们的思想。在脑残们一代接一代的努力下,他们硬生生地把鲁迅的思想经典变成了语录经典,随便哪一段话、甚至某个标点符号,都生搬硬套地安上一大堆“重要含义”,然后逼迫学生们背诵。没准鲁大叔当年只是随手一写,但到了学生手上就变成了至高无上的圣典,由长老们解读出一堆又臭又长的歪经出来,而且翻来覆去地考试,让你躲都躲不过去。
其实这种事情在成人世界里很常见。最高领导随便几句话,党校的八股教授们都会拓展出一堆又一堆所谓重要含义,上下一齐诚惶诚恐地写心得,谁都知道是狗屁,谁都靠着它吃饭,谁也不敢说什么。但拿鲁迅的文章去欺负学生,教育部实在是缺了大德,因为经过几轮摧残后,学生们统统对鲁迅的文章起了阴影,谁的文章都可以读,就是不肯读他的文章,也无从理解他的思想。没有人明白他对民族国家的忧虑思考,而读不懂鲁迅对家国沧桑如火的煎熬,也就无从体验那一份人格的伟大光辉。
教育部的办法很邪门,但是也很管用,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甚至还可以说是为学生“好”,因为谁要真读懂鲁迅的话,对他和社会是比较危险的。
太有思想的人不利于说教,也不会真的听话,文化部又要树鲁迅的典型,又要防学生有思想,只好想出这种损招,也真是难为了他们。当然对学生们来说,不读鲁迅未必是一件坏事,因为很多时候思想统制是件极其严酷的事情,穿件“不自由宁毋死”的汗衫也要坐牢,还经常有说错一句话导致全家遭殃的年代,真的读懂鲁迅不仅给领导们维稳出难题,对自已也是非常吃亏的。
所以,我们只能继续麻木。
虽然鲁迅很伟大,但他毕竟只是文人,指得出问题却不能解决,真正说话算数的还是手里有枪的各路军阀。而一九二八年的蒋司令显然不会在意市民对中山陵的看法,更不会研究鲁迅对他们的评价,委员长要操心的是他现在位置很不稳,主要是周围的实力派(其实还是军阀)太强大,不仅仅是功高震主,简直是要把主人硬生生挤下台去。
坐在办公室里,蒋介石忧心冲冲,坐在家里,蒋介石还是忧心冲冲。这时身边有人告诉他说:蒋老大,其实你不用这么难过的,我有办法。
蒋介石眼前霍然一亮。跟他说有办法的人,叫杨永泰。
杨永泰,孙中山的老部下,时人有评,“足智多谋”。
虽然人很聪明,虽然人很有名,杨永泰却一直是个配角的地位,主要是因为他比较背运,几次找主人都找错了对象。先是跟孙中山搞革命,后来看到西南军阀势力比较大,就跟西南军阀眉来眼去,最后哪也呆不下去,跑北平去找北洋军阀求进步,每次的新东家都很快倒台,最后连自已的饭碗也倒腾没了。
三姓家奴、背弃孙中山,种种不大好的名声都如影随形,钉在他的身后。杨永泰想在新政府里找个差使,万言书递到李宗仁那里,什么反应也没有,杨永泰知道,李司令嫌他朝三暮四。
无所事事的杨永泰只好另投门路。幸好他同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关系不错,在熊式辉的推荐下,他找到蒋介石,试探着想看委员长的态度。
经过几轮白眼和冷落,杨永泰对前程已经不抱太大希望,没想到蒋介石听说他想投奔,立刻大开中门,热烈地张开双臂迎了过来:欢迎你来我这里上班,欢迎!欢迎!
转载自天涯:红潮笑笑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