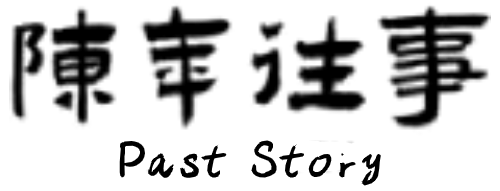鲍罗廷指名道姓的时候,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,不是他的下属,也不是他的学生。
在场的几百人都是大惊失色,因为他们知道以蒋司令的性子,是绝不会对这种事情毫不在意的。
蒋介石果然被鲍罗廷的言辞激怒了。从调职、迎汪到宴会的羞辱,一切都显示武汉等着他的绝不是鲜花和欢迎队伍,而是赤祼祼的陷阱。他没有多说什么,满脸怒气地“吃”完了这顿饭,然后扬长而去。
鲍罗廷的这次宴会,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号,距离大家彻底分手,还有三个月时间。
在共产国际和武汉中央的强大压力下,蒋介石终于还是去了一趟武汉,完成一系列仪式之后,蒋介石继续以总司令的身份到前线北伐,留下一帮意见纷纷的中央委员。
由于两年来蒋司令树大招风,加上他做事情确实比较有问题,鲍罗廷和其他反对派成功占领了舆论阵地,准备召开一次全会,把枪指挥党的局面重新调整过来。
大权旁落的蒋介石当然不会麻木不仁,但问题是武汉中央有唐生智等人保驾护航,而且一举一动都走的是党内程序,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比他高出一头。蒋司令没有别的借口,只能反复声明自已继承总理遗志,是革命的先锋领头羊,谁敢反对就是反对革命,就只能革他的命!
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,蒋介石一直用的是同样的理由。
虽然蒋介石一直没答应去武汉,但毕竟两边没有翻脸,凡事也都在好商量之中,没想到这顿特大号饭局却吃出了问题。为了给蒋介石施加多一点压力,鲍罗廷在吃饭前的演讲里批评了军人妨碍工农发展等不和谐现象,并且直接点了蒋介石的名!
鲍罗廷指名道姓的时候,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,不是他的下属,也不是他的学生。
在场的几百人都是大惊失色,因为他们知道以蒋司令的性子,是绝不会对这种事情毫不在意的。
蒋介石果然被鲍罗廷的言辞激怒了。从调职、迎汪到宴会的羞辱,一切都显示武汉等着他的绝不是鲜花和欢迎队伍,而是赤祼祼的陷阱。他没有多说什么,满脸怒气地“吃”完了这顿饭,然后扬长而去。
鲍罗廷的这次宴会,时间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号,距离大家彻底分手,还有三个月时间。
在共产国际和武汉中央的强大压力下,蒋介石终于还是去了一趟武汉,完成一系列仪式之后,蒋介石继续以总司令的身份到前线北伐,留下一帮意见纷纷的中央委员。
由于两年来蒋司令树大招风,加上他做事情确实比较有问题,鲍罗廷和其他反对派成功占领了舆论阵地,准备召开一次全会,把枪指挥党的局面重新调整过来。
大权旁落的蒋介石当然不会麻木不仁,但问题是武汉中央有唐生智等人保驾护航,而且一举一动都走的是党内程序,不管从哪个角度都比他高出一头。蒋司令没有别的借口,只能反复声明自已继承总理遗志,是革命的先锋领头羊,谁敢反对就是反对革命,就只能革他的命!
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,蒋介石一直用的是同样的理由。
一九二七年,三月。
中央政治会议的几个委员们还在南昌,一直以来蒋介石用尽办法又哄又劝,希望他们看在兄弟面子上不要去武汉,等事情商量出个办法来再说。但是等到此时,武汉已经发来了开会通知,让他们去参加第二届三中全会,讨论党务问题,谭延闿、何香凝等人都在准备动身。
很明显,南昌城池小水浅,容不下中央政治会议的大龙,他们已经要弃蒋而去,投奔武汉的中央了。
死撑了几个月,终于还是没能支撑住,蒋介石很沮丧。他明白武汉的二届三中全会肯定对他不利,多半要清算上次开会的整顿党务案,但又没有理由反对中央,最后只争取到一个条件,就是会议延期几天举行,等他到了再开。
这是一个并不过份的要求,而且蒋介石也确实显示了诚意,派出亲信陈果夫参加准备工作,因此武汉同意把大会从三月一号推到七号。但蒋司令实在太忙,又提出要求说七号太紧,必须再延五天时间,推到十二号。
早几天晚几天其实并不重要,可是为着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,武汉的执委会却发生了激烈争执,并在极其诡异的情况下达成决议,不等蒋介石来武汉,大家直接开会。
之所以说情况诡异,是因为参加讨论的执行委员里面,有七个国民党,却有九个共产党,包括态度激烈的毛泽东。
虽然加起来不足法定人数,共产党人却靠数量优势强行达成了开会决定,连给蒋介石延五天时间都不行。
在共产党员眼里,这种做法叫坚持原则;在历史书上,这种做法叫坚决斗争;在实际效果上,这种做法叫激化矛盾。
在我看来,几万共产党员、几十万国民党员正是被这帮二杆子一步步推上绝路的。
既然延几天时间都不可以,三中全会当然没有蒋介石的份。三月十号,武汉的国民党委员们召开大会,决定取消所谓中央委员会主席,由常委会进行集体领导,并成立所谓军事委员会、政治委员会取代蒋介石。所有一系列决议痛快地把蒋介石的权力一撸到底,甚至连黄埔军校的校长制度都不能保留,张静江之类元老更是下岗分流,赶走没商量。
如此激烈的决议自然痛快,但是效果也是相当明显,蒋介石看到送来的文件后勃然大怒,差点把办公桌都砸了,勉力合作也就成了一句空话。
失去所谓党中央的支持,蒋介石只能下定决心另立门户,在这个方面他相信,自已还是相当有政治资本的。因为北伐军捷报连连,眼看就要攻进南京、上海,如果有这两个大城市在手上,武汉只能算浮云。
从现实角度上讲,蒋介石的考虑有他的道理,所谓中央无非是一帮人开会,愿意拥护自已固然好,不愿的话直接抛开另找一批也无所谓。反正委员不过是个头衔,只要肯开价钱,革命元老、社会名流有的是,毕竟三条腿的蛤蟆难找,两条腿的委员还是一抓一大把的。
三月二十四号,国民革命军打到了南京城,北洋军阀无心抵抗,纷纷四处逃窜。第二天北伐军顺利入城,很快就发生了大规模抢劫事件,城内外国领事馆、侨民住宅甚至教学学校都受到大肆劫掠,英美驱逐舰立刻对南京城进行炮击,炸死炸伤两千多军民,直到抢劫停止才罢休。
蒋介石当然不承认国军会搞抢劫,他宣布所有坏事都是北洋兵混穿革命军制服干的,然后迅速占领南京城,准备把它当成新的首都。
三天后,蒋介石紧急召见张静江、蔡元培、吴稚晖等人到总部行营,密谋逮捕所有共产党分子,施行彻底清党。
打仗时出现抢劫并不稀奇,蒋介石非要把帐算到共产党身上,却着实让人稀奇不已。南京事件之所以会跟共产党联系到一起,不是因为死伤两千多中国人,而是蒋司令担心影响到欧美外交。
由于孙中山和共产党的口号都是反帝反封建,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,如何反对帝国主义就成了国共两党的共同话题。在这个方面国民党作为执政党,要综合考虑实力对比,不能树敌太多,而共产党的顾虑就小多了。按照陈独秀的主张,中国地界上就不该有帝国主义分子,所有租界当然是一律武力收回,外国资本家的工厂更应该全部没收,用最革命的手段对付反革命分子,什么外交、什么条约统统扔到垃圾堆,总之打你没商量。
有这层因素在里面,蒋介石对共产党实在是头痛之极。事实上占领九江、汉口之后北伐军武力收回租界,已经引发了极严重的后果,再不控制将导致英美军队介入,北伐军势必腹背受敌。对蒋介石来说,同共产党翻脸是迟早的事,苏联援助即将断绝,如果再同英美列强闹翻,他将变成彻底的孤家寡人,被自已掀起的洪流活活淹死。
蒋介石很有紧迫感,是因为早在三月二十二号,共产党人经过前后三次工人暴动,已经先行占领了上海,新的临时市政府拥有独立武装,正在同他的北伐军对峙。
本来工人武装同北伐军算一家人,可是蒋介石派去联络的总指挥实在有问题,他的名字叫白崇禧。
作为桂系骨干、民国杰出的军事专家,白崇禧的一辈子都跟共产党过不去,甚至他的老搭档李宗仁后来回归大陆,他的立场也没有丝毫改变。派这个人去和共产党打交道,蒋司令的用意那是相当不良。
蒋介石对上海反应如此过敏是有原因的。一直以来,共产党不过是地下组织,定期搞个流行示威之类小活动,并不能算独立的力量。但上海的成功意味着他们开始掌握军队和武装,而且一次能占领一个大城市,普通军阀都不是对手。
上海有国际港口,只要共产国际愿意,马上苏援军火就会象潮水一样涌进来,训练有素的共军同全体秘密党员一道,可以在瞬间把他打得落花流水。如果没有估计错,共产国际已经把枪炮打包装上了船,正在去上海的路上,自已正面临着两线夹击的危险,覆灭只是早晚的事情。
必须夺回上海,否则死无葬身之地,在最危急的关头,蒋介石派出了白崇禧任总指挥,前往上海收拾局面。
果然白指挥一到上海,立刻同共产党发生了严重冲突,陈独秀也不示弱,宣布要收回租界(此前一直说是尊重租界独立地位),把租界里的难民吓得狼哭鬼嚎。白崇禧则一面把亲共的薛岳调开,一面下令如果工人敢捣乱,军队就要开枪镇压,绝不留情。
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把上海当成了左右派决斗的战场。共产党手上的武装纠察队只有两千多人,却号召要在短期内扩招五万党员、成立军队同“反革命右派”蒋介石彻底决裂,完全占领全上海,如果不是莫斯科发现事情不妙紧急发电报来降温,两边随时可能爆发大规模火拚。
武汉中央支持上海政府,蒋介石却明显反对,两家已经到了分裂的时机,战事一触即发;就在这危险关头,一年前被逼出走的汪精卫终于来到了上海,执行灭火工作。
从二六年五月被逼离境算起,汪精卫已经在法国下岗了九个月。
一九二七年二月,正在“养病”的汪精卫离开法国,来到了莫斯科。全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头羊、伟大革命领袖斯大林不惜屈尊,亲切会见了这位著名的中国革命左派人士 ,并对汪精卫同志进行了重要的指导和教诲。经过斯老大和风细雨一般的热情会谈,汪精卫同志极大地提高了自已的政治觉悟,并在一系列问题与共产国际达成了共识,具体来说就是一句话:蒋介石下岗,我来干!
汪精卫很高兴。共产国际的支持不是一句空话,而是崭新的卢布和闪亮的枪炮,有共产国际的全面支持,别说蒋介石,就是孙中山从坟里爬出来,恐怕也得排在他后面。他十分高兴地答应斯大林,然后坐上轮船去上海,准备转道武汉当主席。
汪精卫回到国内的时候,整个国民党已经是一地鸡毛,到处在等着他收拾。
武汉中央早在三月份就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,除了新都定在武汉外,还罢免了蒋介石的一切职务。从国民党的规章制度上看,武汉政府的会议非常合法,但蒋司令不是一般人,自然也不会拘泥于投票、选举之类的小事,直接以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了一份《告黄埔同学书》,宣布自已绝不接受决议,有意思的是他的宣言是发给黄埔的军官们的,而不是发给国民政府。
按照蒋介石的说法,身为党员自然要服从党中央的决议,但是同样也要尊重所谓程序正义,具体来说就是党内还有一个中央监察委员会,只要监察委员认为会议不对,就可以宣告无效。
早在一九二四年的时候,孙中山召开一大,就特别设立了一个所谓监察委员会,其地位大概相当现在的中纪委。其他部门都是国共合作,唯有这个部门只收国民党、不收共产党,而且吸收的都是反共派,摆明了是对新入股的小弟不放心。现在,这个小小的借口就成为蒋介石能抓住的唯一稻草。
蒋介石突然如此看重监察委员会,是因为有几个监察委员一直跟随着他,并秘密通过了清理共产党的决议。虽然从各方面来看,这几个人搞出来的决议很可能是事后补办的,不管是参加人数还是会议程序都相当成问题,但蒋司令认为它有效,那就是有效的法定文件,可以推翻党中央的一切决策。
二七年四月二日,汪精卫见到了蒋介石。
一年没见,大家都添了几根皱纹,一群人在孙中山的故居里相互寒暄,回顾已经破裂的友谊。经过一番商量,最后决定四月十五号在南京召开监察全会,此前汪精卫负责通知共产党停止活动,武汉中央的相关命令也暂停执行,所有工会纠察队暂由总司令部指挥,听候会议决定。
一切反对派都停止活动,等监察会议召开后再决定,会议地点南京还是自已的地盘,蒋介石和手下都觉得可以接受,于是他表示服从汪主席的领导,并让汪精卫去找陈独秀协调解决。
正当蒋介石心里稍稍淡定一点的时候,突然听到一个消息,说武汉中央已经把蒋介石撤职查办。大家当然是勃然大怒,立刻跑来找汪精卫大发雷霆,痛骂鲍罗廷和共产党不是东西,吴稚晖还说,他的监察委员会已经提了一个弹劾案,要清理共产党,而且这个提案已经通过,没有商量的余地,告诉汪主席不过是通知一声!
这么重大的事情还没提出来就已经通过了,汪精卫很是不以为然,脸色也极其难看。眼看要不欢而散,李宗仁等人赶紧在一旁打圆场,最后汪精卫提了三条建议:一、他可以跟陈独秀商量保护租界的问题;二、武汉的军政命令可以先不执行;三、如果情况紧急,可以临时处置各地共产党和工人队。
听到汪精卫的建议,大家都松下一口气来,两家又重新达成了协议,并由汪精卫负责找陈独秀去落实方案。
从表面上看,革命再次实现了暂时团结,但蒋介石的口风已经大变,从“服从汪主席领导”变成了“一切由监察委员会决定”。大家都明白,这次蒋司令是要动真格了,因为十二个监察委员里有七个在他身边,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想要的提案。
汪精卫当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,因此见过蒋介石之后,他马上就找到了陈独秀。看过蒋介石的条件后,他和其他人都是大惊失色,经过激烈研究,最后决定两个人代表两大政党也发一份宣言,共同回顾几年来的历史友谊,重新申明合作诚意与革命志向,并表态一定要协手共进,把革命进行下去。
事实证明,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宣言。有了这份宣言,汪精卫的国民党才能同共产党人继续保持合作,武汉政府靠着它延长了百余天的生命,无数人也因为这百余天,在后来的那场风暴里幸免下来。但汪主席的稀泥神功到此也就为止了,因为他只能让陈独秀承认不侵犯租界,实在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接受蒋介石的领导。
同陈独秀发完宣言,汪精卫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去武汉,主持摇摇欲坠的大局,而蒋介石则是勃然大怒,因为他发现这份所谓联合宣言虽然说要尊重租界,却只字不提服从蒋司令(或者国民党)的军政领导,很明显不是汪主席疏忽错漏了,而是共产党压根不肯服从两家的临时协议。恼火的蒋介石马上去找汪精卫,却发现这位汪主席滑头得很,已经离开了上海,他只能在报上发表两个人先前的协议,以防赖帐。
汪精卫去武汉,蒋介石很失落。
他说自已服从汪主席领导的时候,前提是汪精卫要留在上海、南京一带跟他在一起,如果汪主席跑到武汉,肯定会跟反对派一齐反对他。没想到汪精卫实在精明,看到他跟陈独秀立场相差太大,竟然悄悄开溜了,先前的种种计划也就成了泡影。
一旦汪精卫站稳脚跟,以国民党中央的身份发号施令,肯定会对他有严重的不利影响,蒋介石相信,他同武汉、共产党之间已经没有合作的余地,除了翻脸无情之外,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
四月九日清晨,蒋介石正式入驻南京城,大批暴徒随即捣毁国民党(没错,是国民党)江苏省党部、南京市党部,迅速控制了整座城市;同一天上海的国民党总政治部也被捣毁,理由十分离奇,叫做“丧失本军信用,阻碍北伐大计”。
对蒋介石的嚣张,陈独秀和共产国际都很镇定,因为他们相信,绝大多数工农分子是拥护共产党的,各地政权组织及党部也是拥护共产党或武汉左派的,蒋介石不过是一帮丘八的临时代言人而已。即使大军在的时候横行一时,只要离开驻地,基层组织很快又会转向自已一边,反动右派的进攻不过是一时之勇,无法在当地扎下根来,因此无需太过担心。
从表面数字上看,共产国际的考虑是正确的,而从实际效果上看,却是完全错误的。
虽然广大群众十分拥护工农运动,但蒋介石也早就发现,只要他的北伐军采取比较缓和的政策,就能得到中间阶层的拥护,在地主和资本家、帮会支持下,一样可以组建所谓党部工会。普通工农人数确实多,可是他们没有枪,只要用“适当”的手段,成立自已的基层政权并不难,也不需要共产党插手。
本来这个秘密用处并不大,因为另立政权等于反叛中央,他一直没下这个决心。但是自三月份武汉突然撤掉他的职之后,蒋介石意识到地盘的重要性,立刻以紧迫的速度扶持各地中间组织,怂恿他们跟共产党农会、工会大打出手,甚至出动军队直接介入,强力组建自已的各级政权。而江浙等地的财团本来就怕工人造反,对执行缓和政策的蒋司令自然是欢迎之至,也同意用各种办法报效支持(主要是钱),保证北伐军不执行共产党那一套过火政策。到四月份的时候,蒋总司令已经拥有党政军各级组织,不再需要武汉的指手划脚了。
占据南京的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,不再跟汪精卫废话,同时跟武汉和共产国际决裂,自立为国民党最高领导。
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号,大批流氓突然骚扰上海的工人纠察队,很快发生武装冲突,早有准备的戒严司令部立即下令,由于共产党人的主动攻击(?),国民政府同共产党宣告决裂,正式清共。
训练有素的北伐军开始大开杀戒了。武装纠察队很快被打散,枪支被收缴,失去保护的共产党和工人立刻成为屠杀目标,草草审讯甚至不经审讯就枪毙。
在蒋介石的命令下,屠杀大潮很快传开,从上海到广州、广西四处是密探和警察,一车车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被抓走刑讯,监狱里传来惨绝人寰的哀号,有的死了还有机会收尸,有的就消失在茫茫黑夜里。凡是蒋司令控制的地方全是血雨腥风,城头挂满示众的死尸和人头,一贯和蔼的蒋司令红着眼睛,指挥各路手下不要手软:共产党都是秘密党员,凡是嫌疑分子尽管错杀,不能放过!
在几十年革命生涯里,蒋司令常常给人优柔寡断的印象,孙中山总觉得他碰到困难就想跑,汪精卫也说他老闹小孩子脾气。谁也想不到,面对无上的权力,蒋介石突然变成了一个比谁都凶狠的魔鬼。
从一九零八年加入同盟会起,蒋介石就在枪林弹雨里面讨生活,还亲自参加过暗杀与暴动,深知乱世中的丛林法则。既然自己主动撕毁了国共合作条约,那就只有把对手彻底消灭掉才能安生,所谓斩草不除根,春风吹又生,这个道理蒋介石是非常明白的。
于是一阵又一阵屠杀惨剧在南方上演。先杀工会、农会,再杀学生,接着很自然地,各派开始把看不顺眼的人相互当成共产党杀掉,杀,杀,杀,再杀。
四月十八号,中华民国新一任国民政府在南京自行成立,伴随着一阵又一阵刑场传来的枪声,蒋介石宣布武汉国民政府自即日起非法,并自我任命为合法的国民党主席。同新政府一齐诞生的,是蒋司令签发的一份长长的通缉令,名单上一共一百九十七人,从陈独秀、汪精卫算起,所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武汉中央全部包在里面,一个都不能少!
比起蒋介石的杀伐决断,汪精卫就迟钝多了。
一直到四月十九号,武汉国民政府还按原计划举行北伐誓师,要向河南的张作霖进军。这时风声已经变了,从上海南京传来的坏消息一个接一个,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,直到有人带来南京政府的第一号通缉令,汪精卫和陈独秀弄了半天才明白过来,原来蒋司令真的反水了。
形势如此急迫,大家都没有心理准备,想不到蒋介石清党的手段如此毒辣,几乎把东南部分的基层组织一扫而光。大家乱哄哄地忙了半天,终于在四月二十二号,中央委员们反应过来,发了一个毫无用处的讨蒋声明,号召大家除掉蒋介石(依照中央命令,去此总理之叛徒,本党之败类,民众之蟊贼)。
这个时候共产党的局势还不算太坏。虽然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广西等地方损失惨重,但武汉中央始终在汪精卫手上,谭延闿、朱培德、唐生智、张发奎等实权人物都没有参与反共,而是把军队调往东线同蒋介石对峙,如果武汉各派能齐心团结,眼前的危机并不是很难应付过去。
可是他们偏偏没能应付过去。
不是武汉各派的实力不够强大,而是斯大林的智商已经余额不足,滑落到跟节操一样的低水平上了。
从占领湖南湖北时起,共产党就大力推行工会、农会,组织工农团体维权,这本来是好事,国民党也没有太多干涉。但共产国际的革命要求实在太高,工会农会也就随之迅速变味,工会很快成了法外之地,不仅拥有自已的武装,还可以随意抓人甚至杀人,相关要求也由适当上涨工资(这个是国民党也赞同的)变成了天价工资,甚至把老板抓起来杀掉;农会更是离谱,由于农民的运动积极性不高,农会大量吸纳流氓加入,这些人先是反对所谓“土豪劣绅”,接着随意把地主都划为土豪劣绅反革命,大批有名望的乡绅没有必杀的死罪,却糊里糊徒地做了刀下鬼。
农会无法无天,是因为斯大林认定,中国革命形势不是小好,是大好,好到了可以实施土地革命的地步。减租减息一类活动已经不再适应现有模式,共产党人应该与时俱进,象苏联一样大开杀戒,闹得越激烈越好,凡是剥削农民的都要“用刺刀刺死”(鲍罗廷原话),才能消灭反革命的基础。
反革命的基础有没有被消灭不知道,不过共产党的基础很快被消灭却是真的,因为此时保护共产党、对抗蒋介石的正是湖南湖北的军队。那些军官大部分家里有几亩田地(没钱也读不起书),听说共产党乱打乱杀地主全都炸开了锅,纷纷要求上级采取措施,保护家小不受侵犯,整个左派顿时吵成一团。
共产国际的指示乱七八糟,一直搞农民工作的毛泽东却很高兴。因为他发现农民运动实在是好搞,只要在农村发动流氓痞子乱打乱杀,造成一段时间的“恐怖现象”(这是他的原话),就可以树立农会的权威,并在最短时间里武装出一支农民自卫军,不必受国民党的节制。
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,制造恐怖现象是共产国际推行的方法,毛泽东的“先进经验”虽然看上去不大厚道,却属于革命探索的一部分。要到后来开辟了苏区根据地后,毛泽东才能因地制宜,自主研究出土地改革的合适手段。
探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共产党人在农村胡搞,国民党立刻紧张起来。口袋里没有多少本钱,身边却在四处起火,汪精卫和蒋介石都很紧张,相互垒起工事,把枪口瞄准对方。
但他们虽然紧张,还有工夫坐下来喝茶,压力最大最不知所措的,是一个大兵都没有的陈独秀。
四一二屠杀发生之后,共产国际很狼狈。
长期以来他们一直给国民党输送大批枪炮,要共产党人配合革命,结果革命没有成功,自已却成了革命的对象。形势已经坏得一塌糊涂,但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,活下来的人仍然要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,也仍然要研究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问题。
从理论上讲,陈独秀有六万共产党员,有不少还是军人,同蒋介石似乎有得一拚。但这六万人都散在各处,平时拉出来游个行还可以,真要打仗一点战斗力都没有;汪精卫对共产党也不知道会友好多久,一旦他也反水,那就真的是全盘皆空,广阔的中国将再也没有共产党的容身之处。
这样的局势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的革命进程,更严重影响了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威信。面对一地鸡毛的严重情况,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决定,大家紧急开会,研究问题根源和解决办法。
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号,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片苦雨凄风中开了幕。情况不好大家都知道,不少人的亲友都失陷在上海或别的地方,凶多吉少,所有人都以急切的心情研究了两个问题,一是怎么会出这种事,二是怎么解决这种事。
这是一次很搞的会议。说它很搞不是幸灾乐祸,而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没一个真正研究出来答案,当然也没一个能解决的方法。
大会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:怎么会出这种事情?
陈独秀有一肚子怨气要发。一直以来他都在要求共产党人搞自已的军队,不能全靠国民党掺和,结果共产国际的几个大爷除了摇头就是摇尾巴,终于摇出了天大的乱子。他很想问问共产国际的几位马列主义二把刀,此时有什么感想,是否还觉得他错误呢?
但是他根本没机会问,因为开会前已经有人做出了结论,他的任务只是听命令而已。
对这次大会的结果,大概可以归结为如下说法:党组织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,帮助陈独秀认识了他的右倾路线错误 ,但陈独秀没有正确对待这种帮助。
从表面上看,这种充满官僚味的样板话没什么用处,就象说陈独秀开车开错路了,大家要他再开回来一样。想要真正明白这几句话的含义、知道字里行间的杀机,同时也了解一点体制内的游戏规则(郑重声明,仅限于当年的斯大林式政党,请勿与现今联系,否则引发后果本人概不负责),我们就必须先理解几个名词。
第一个名词叫组织。
组织本来是从日语传进来的外来词,但到了中国就发展出了另类的含义。但凡一个人入了党或团,就变成了有组织的人,背后有一大帮兄弟撑腰,出了事还有人帮你摆平,听上去感觉很不错。
很多人以为是自己拥有了组织,但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,因为实际的效果,是组织拥有了你。
从加入组织的那一天起,你思想要靠拢组织,行动要依从组织,还要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,接受组织里职务比你高的人指导。组织当然也会关心你、爱护你,替你决定你生活中的大小事情,例如结婚、工作、调动之类,当然被关心的人必须接受组织的好意,绝不能不识抬举。
组织是一个抽象的名词。笼统地说,凡是在党内,一个人职务比你高的话,他行使权力的时候就可以自称组织,而在他代表组织行事的时候,你千万不能反抗,否则就是对抗组织。
对抗组织,罪名是很严重的,除非你的后台比他硬,否则一定死得没商量。因为当一个人或几个人自称组织的时候,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已,而是代表着光辉伟大的党,在那一刻他不再是一个人,而是继承了共产主义革命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、与无数风雨同舟忠贞不二的先辈化为一身,有着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等伟大革命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的思想精髓附体,是受最光荣、最正确的工人阶级先锋政党委派而来,他的每一句话都意味着真理与服从,他的每个行动都指导着人类最高理想与神圣革命的最终方向,当你面对他的时候,你面对的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的权威与指令,执行着最神圣最光荣的任务,谁要说不就是同全人类为敌,势必天打雷轰、不得好死、全家遭难、遗臭万年。
所以有点政治经验的人,对组织两个字都会极其敏感。只要一提到组织,大家全都一致欢呼歌颂,但只要仔细看一下,就会发现这帮人同时又在用最阴寒、最森严的心态去防范这两个字。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态度出现在同一个时刻,实在也是种离奇的现象。
共产党员可以不怕死,可以挨饿受冻,可以无畏地堵枪眼、顶炸药包、面对酷刑死不招供,但没有多少人敢对组织说一个不字。
我们在后面会看到,组织这两个字有多么可怕的魔力。在下属们面前,组织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,它可以凌驾一切法律(哪怕是自已定的),撕毁所有约定,违反任何承诺,无论它的要求是否合理,都必须不折不扣地照章完成(学名:党性)。在组织里捞一个适当的位置,可以贪污纳妾(向忠发),可以随意用各种酷刑杀人(夏曦),可以找漂亮女人睡到一个炕头谈思想工作(邓力群),甚至可以把别人的老婆剥光衣服玩集体性虐待(李韶九);最妙的是除非你的地位下降了,否则法律对你几乎是没有约束力的,谁也奈何不了你。
第二个名词叫帮助。
帮助本来是件好事,例如说家里没酱油了,邻居帮忙送半勺来解炒菜的急,这就叫帮助。
但如果是组织来帮助你,那就千万要小心了。组织通常没工夫去帮助别人,而只会接受别人的汇报与奉献,组织主动去帮助你,往往都不会是什么好事。
在组织的定义里,每个人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螺丝钉,是在组织的旗帜下前进的,每个人都有义务紧跟组织,在组织的带领下向共产主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当然你的水平永远不能也不可能超越组织(要不然组织就得听你的了),只能努力向组织靠拢,并且发自内心地、无私无怨地向组织奉献你的一切,如金钱、青春、劳力等,个别情况下被组织里的上级看中了,为革命事业照顾首长起居也是应有的觉悟。
换句话来说,你应当是永远紧跟追随组织又永远不超越组织的角色;只要你能守好本份,组织也会大开方便之门,开恩收下你的奉献,让广大象你这样有上进心、但水平和觉悟都很低的笨蛋有幸提高思想认识,在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提携你这种不成器的小东西荣耀前进,前提是你必须认清形势、端正认识,永远同组织保持立场一致,不至于成为迷途的羔羊,同历史的强大车轮对抗,堕入革命事业罪人一类万劫不复的东西中去。
所以如果你一切都正常的话,你是不需要组织的主动帮助的,你应该自已去了解组织、适应组织。如果要等领导百忙中放下手头的事情,暂停在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飞速前进的步伐,代表组织来“帮助”你的话,那一定是出了严重的问题。
什么问题先不重要,你必须先忏悔自已一贯的低能、阶级局限性与私心虚荣心,影响了组织的革命进程与共产主义事业,然后再来向组织请示,自已哪个立场没站对,并在得到指点后恍然大悟,痛哭流涕作感谢状,保证一定改正错误,请组织放心和监督。
这才是组织意义上的帮助。我们会在后面看到,在那个年代里,凡是不接受这种帮助的人,通常下场都不会太好,轻则精神失常或严刑拷打,重则诛连九族,最极端的时候,不仅自已倒霉,连家乡都要划成另类。
第三个名词,也是惊心动魄的罪名,叫路线错误。
党组织永远是最光辉、最正确的,也永远代表着政治上的最先进,但党在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,总难免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,而且奇怪的是,好象从来就没有如意过。
当然挫折原因总是多样的。起点低,基础薄弱,群众落后,敌人太强大,天灾收成不好,自已长得不够帅,这些都是理由。但有时种种理由都不怎么成立的时候,组织往往会发扬强大的纠错能力,回过头来检讨自已的所作所为,而检讨的结果,向来都是恍然大悟,原来党还是正确先进的,马列主义(请依各国国情酌情添加相关思想或理论后缀)也绝对不可能有错,但是落实到某个人身上,这个人的水平出了差错,把党带错路了,所以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
因此所有的错,都不要由党负责,党能发扬纠错能力查出这个人的问题,反而更是值得欢呼雀跃的大好事,说明党更加进步了,水平也更加提高了。这对党当然是件好事,但对那个人和党认定的同伙,就绝对不是好事了。
党是不断犯错误、又能够自己纠正错误的,纠正错误的主要方法,就是把错误推到某个人身上去,然后归结成他的错误路线(张国焘语)。对于党员来说,什么错误都不要紧,最怕的就是“路线错误”,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,就意味着坏事全要由他负责,不仅要背负着无法洗清的罪过,而且有了这个历史性错误,将来就是怎么努力效忠,也很难有机会摆脱头上的大帽子,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
“路线错误”同“分裂党”一样,都是二十万伏高压电级的利器,一触即死,诛连九族,百年定论,罪过千秋,万劫不复。
最后要理解的一个名词,叫正确对待。
有上面的说明,其实也不用多加解释了。党说什么就是什么,组织认为谁不好,谁就必须承认自已不好,而且认罪要比组织更加积极,才是正确的态度。但凡在被坑、被扣黑锅的时候喊冤枉,都属于错误行径,是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帮助的典型表现,也是背叛伟大光辉共产主义事业的严重罪行。
看完这几个名词的解释,再回过头看陈独秀,就能明白他在五月份的处境了。党组织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,帮助陈独秀认识了他的右倾主义路线错误 ,-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其实就是说,共产国际认定出事的原因是陈独秀不够强硬、对国民党右派坚持不住原则,所有的牺牲和损失都跟共产国际没关系,主要由陈独秀负责,而中国共产党决定同共产国际一起,给陈独秀强扣这些罪名。
一直以来,陈独秀都是以路人甲或小兵乙的形象出现的,他的身份只是配角,形象也不大光辉。因为从本质上讲,他只算共产国际下属分支的一个办事员,正所谓丫环拿钥匙,当家不作主。有共产国际支持的时候,他是全能的总书记,一言九鼎;但被共产国际抛弃的时候,哪怕他文武双全、高风亮节,哪怕他忠于共产主义、两个儿子都在挑革命大梁,都不过是一个弃掉的棋子,眼睁睁看着所有的同志抬起腿来,往他屁股上狠狠踹上一脚,作为对共产国际表白的心迹。
从二三年到现在,陈独秀的所有事情都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下进行的,共产国际说应该早点注意的事,他当年全都提出来过;现在对方居然倒打一耙,把脏水全泼到他头上,最坑爹的是其他人全都接受共产国际的说法,把他当成了咩咩叫的替罪羊。
陈独秀没有党性,因为他的觉悟不够高,或者说风格不够下作。
从本质上讲,他仍然是个典型的中国文人,骨子里还是当年编《新青年》的那个热血愤青,他算文人也算政治家,唯独不算搞党务的政客,自然也不能接受官僚政治的潜规则。
面对咄咄逼人的压力,他做出了自已的选择:绝不指鹿为马,绝不曲意逢迎,绝不替斯大林背黑锅!
侠骨霜筠健,豪情风雨频,陈独秀的两句诗很能说明他的性格。他不是一个好的总书记,也不是符合组织要求的党员,但他仍然是一个守良心的中国人,是守着数千年气节的文人,一个讲真话、办实事,不肯冤枉人,也不让人冤枉的有骨气的中国人
在那个腥风血雨的日子里,陈独秀拒绝了党务政治的压迫,不肯说假话去维护领袖的所谓光辉。他成功地坚持了自己的气节,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
共产国际已经不再需要他了。
既然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,那么为了领袖的形象,找个替罪羊、换个人上马,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在开会以前,他们早就跟瞿秋白等人碰过头,并且达成了完全的共识。
瞿秋白本来是一个对俄国文学感兴趣的小青年,去俄国采访后改信共产主义,后来成为鲍罗廷的中文翻译。在广州的小小办公室里,矍翻译曾经和一位鼎鼎有名的越南青年共事过,那位越南青年叫胡志明。
因为跟共产国际走得太近,不能很好衔接共产党中央的指导思想,瞿秋白也碰到了两头不讨好的情况,被召回上海做陈独秀的俄语翻译;由于经常接触马列著作,此时他已经混到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头衔。几年来一直同陈独秀亲切合作的鲍罗廷明确告诉瞿秋白,中国的一切虽然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的,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承担失败的责任,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会影响到世界革命,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,更会使中国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。总而言之一句话:领导丢面子,后果很严重!
为了使共产国际能顺利领导世界革命,为了使全世界劳苦大众早日得到解放,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,背起这个黑锅。当然,这一切不是没有回报的,只要能做到这一点,共产国际愿意继续支持中国共产党搞革命,直到最终的胜利。
鲍罗廷口水横飞,几个政治局委员连连点头,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以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,勇敢地承担下了替罪羊的光荣任务。在和鲍罗廷商量的时候,瞿翻译干脆赤祼祼地表示,如果革命失败的责任归到整个政治局身上,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威信就会集体破产,损失实在太大;既然陈独秀有重大过失,现在态度又不够端正,不妨把全部的失败责任,推到他一个人身上。
对瞿翻译的觉悟,鲍罗廷十分赞赏,完全赞成。于是陈独秀的命运就此决定下来。
这些密室里见不得人的话,原本是死也不能让外人知晓的,但政治局的听众里有个人后来到了国外,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,并坦然地承认自已也在里面扮过不光彩的角色,这才使真相大白,那个做事认帐的人叫张国焘。
共产党的五大很容易地给陈独秀下了定论,解释并解决了革命为什么失败的问题。根据几个人的密室决议,陈独秀被扣上右倾主义的罪名,承担断送革命的责任,活着被人唾骂,死了也不能解脱。他死后六十多年,全中国(台湾地区除外)的教科书仍然教导下一代说:陈独秀,新文化运动倡导者,右倾机会主义分子。
作为一个拒绝官场潜规则的文人,个人认为,陈独秀无愧中华民族“新青年”的称号。
五大可以批判陈独秀,可以给他背黑锅,但光靠整人是没有用的。面对危急的局势,政治局必须给全体党员一个交待,指一条明路才行。
这一点不难,至少对坐在办公桌前指挥世界革命的斯大林来说,一点也不难,因为斯大叔心中早就有了答案,叫做汪精卫。
斯大林对汪精卫的印象很好。
在他心目中,汪精卫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代理,十七岁参加反封建革命,一直就是亲共人士,而且道德形象极为理想。汪主席当年是民国四大帅哥之一,读书时女生尖叫指数就超过一百,却从不乱搞、从不纳妾,非常符合正人君子的形象标准。共产国际反馈来的信息也很乐观,汪精卫虽然不代表工人阶级,但可以归到偏左的小资产阶级阵营里,这样的人做盟友比做下属还要合适。
斯大林同志的思路其实很简单,他只是算了一下加减法。蒋介石是右翼,共产党和汪精卫算左翼,再加上工农阶级的数字,两边对比一下,就得出了非常乐观的结论,因为反动的蒋介石势力远远低于进步的左翼汪精卫。
原来东风还是压倒西风的,那还担心什么?!
主宰中国革命的竟然是如此弱智的计算,实在让人哭笑不得,但不管我们信不信,反正斯大林是信了。考虑到他老人家要指挥全世界的革命形势,实在没有太多工夫为中国操心,能做这么多算术题,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。
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也参加了大会,并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,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。在大会上毛泽东表示,目前应该搞土地革命,彻底分掉地主的田,吸引农民参军。
毛候补的想法非常激进,可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同意,这也成为后来他们被反复批评的理由。但我们要知道的是,反对毛泽东并不是陈独秀进步不够,而是根本没有可行性,如果共产党调头去搞土地革命,汪精卫和国民党将不得不翻脸,立刻湖南湖北就要乱掉,全体共产党员马上被一锅端,再也没有后面的开国大典了。当然,多年后的清算工作也在所难免,他们都因为这个被划成了右倾路线。
应该说汪精卫在团结工作上还是很上心的。共产党事先和他通报了内容,汪主席专门到场讲了话,表达自已对国共合作的坚决支持和坚定信心,大家都热切鼓掌,相信革命形势依然大好,前途也依然光明,一定能战胜反动军阀蒋介石,北伐成功,三民主义统一中国,然后再来一次共产主义大暴动。
在一片打气声中五大“胜利”而莫名其妙地闭幕了,给了一堆决议,没解决一个问题,批了一顿陈独秀,却又强留他当总书记。
虽然都知道陈独秀要倒霉,但党还在风口浪尖上,所以陈总书记余热未尽,依然被押到了前面,替大家挡箭。
开完五大,共产国际长舒了一口气。他们终于把黑锅扣给了陈独秀,现在要考虑的是下一步该怎么走。
在这个问题上,汪精卫有着同样的疑惑。
武汉的国民党人大都是左派,因此对工农运动也都是支持态度,但随着时间的发展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现动摇,首先提出意见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。
由于宋子文后来成了蒋介石的大舅子,又是“蒋宋孔陈”四大家族的重量级人物,因此宋部长的名声一直不大好,经常作为反动派头目形象出现。但必须说明的是宋美龄此时还没有嫁人,宋子文办事还是靠谱的,对工农运动也相当积极,此时跟蒋介石并没有特别的关系。之所以对主旋律有反对意见,是因为宋部长管钱,而工人搞得他手上越来越没钱。
自从共产党人进驻之后,整个湖北的群众运动相当火爆,武汉城里的工会有如雨后春笋,发展得异常篷勃。工人们竞相要求提工资,上班时间忙着搞革命游行,天天拿着武器四处巡逻,甚至随意抓人杀人,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秩序。
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,钱只有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才能生出更多的钱。打仗时交通阻隔已经有相当影响,此时工厂又全线减产亏损,财政情况当然是一落千丈。
俗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,宋子文是大当家,所以他知道柴米油盐很贵。湖北省的税收已经跌到每月不足三百万的地步,可是武汉政府的开销却是一千两百万元,宋子文顿时头大如斗,不得不提出约束政策,希望能稳定财政收入。
应该说宋部长的出发点绝对是好意,也没有欺负工人的意思。但是各级工会却不买帐,甚至下级工会对总工会也是阳奉阴违,都只管扩大自已的势力,听说宋子文提了他们的意见,顿时恨之入骨。宋部长见势不妙,工人们做事又野蛮不讲理,只好卷起铺盖离开武汉,到蒋介石那里研究财政。
讨厌的宋子文走了,工会仍是继续要求涨工资,政府收不上税,只好拚命印钞票发债劵,物价马上随着上涨;于是又提出要涨工资补贴生活,最后陷进恶性循环里。武汉政府吃了上顿没有下顿,很快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。
没有钱已经是一件要命的事情,国民党还有更加大的麻烦要应付。由于各地都号称要反抗帝国主义,大家纷纷攻击外国人,眼看要引发列强武力干涉,汪精卫、谭延闿等压力实在太大,只好来找陈独秀商量,十分委婉地建议共产党做事注意一点分寸;尤其是农民运动影响到很多湘军,既然大家都是盟友,最好搞个章程一致行动,不要弄得太过火不好收拾。
一贯联俄联共、扶助农工的汪精卫竟然反对农民运动,听上去实在不好想象,事情的原委要从基层农会说起。
国共合作以来,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处大量成立农会,号称维护贫困农民的权益,这一点自然是值得赞赏的,也得到汪精卫、朱培德等人的广泛拥护。问题是,如何能吸引识字不多、又听不懂革命道理的落后农民参加农会、拥护党组织呢?
在这里不妨做一个实景推想。假设村里有地主张三,手下的佃户是李四和王五,那么如果要搞革命,外来户共产党当然是吸引李四和王五组织农会,平分张三的地。
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长久的。一来张三会去找官府说理,官府可能会凭地契宣判李四和王五非法;二来就是官府不管,李四和王五拿了地会感激你,但也只是感激你让他过得好一点、做农民更安生,多半不会为这个给你卖命,而且哪一天如果你走了,张三回来只要施点压力,李四和王五就会把地还给张三。
在党八股的术语里,李四和王五的行为叫农民阶级的狭隘性与革命的不彻底性,通俗一点地说,就是农民只想过日子,不想革命掉脑袋。
所以要搞农会,光减租分田是不够的,必须让农民死心塌地明白,不紧跟自已就没有出路,连先前的农民都当不回去。具体办法也简单,主要来讲是让流氓带头,组织农民搞运动,想办法折腾地主,斗得越狠、两边仇恨越深,农民们就越会跟自已走,一开始是分财、给地主们戴高帽游街,到后来大家斗起性子,索性一杀了事。
应该说有的地主确实罪大恶极,毙了也不冤枉,毕竟为富不仁的事情有不少;但也有不少地主并没犯死罪。当然革命领袖是不会关心罪不罪一类小事的,只要能让农民斗出劲头就行,大家爽起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,等杀过人了再去告诉他杀得对,革命支持你杀反对阶级,下一步自然是坚决革命、抵抗敌人的反攻倒算,想回去当农民也真的不行了。
毛泽东最引以为豪的是自已的土地革命,汪精卫最头痛的就是土地革命,陈独秀最担心要出事的也是土地革命。湖南各级军政官员成分都不怎么好,出身贫农的基本没有,大多都是地主家庭,共产党一闹革命,家乡的亲朋好友被斗的斗、杀的杀,城市里的工会则天天罢工要求涨工资到天价,或者要求一天只工作四小时(说老实话,哪国也没有这种福利),弄得从城市到乡村,一片混乱。
这边在真心把地主和资产阶级当成敌人来斗了,那边却还在拿着枪,保证共产党不被蒋介石干掉。面对盟友的无下限无节操,汪精卫发自内心地感到蛋疼:大家都是出来混的,讲点分寸好不好?!
转自天涯:红潮笑笑生